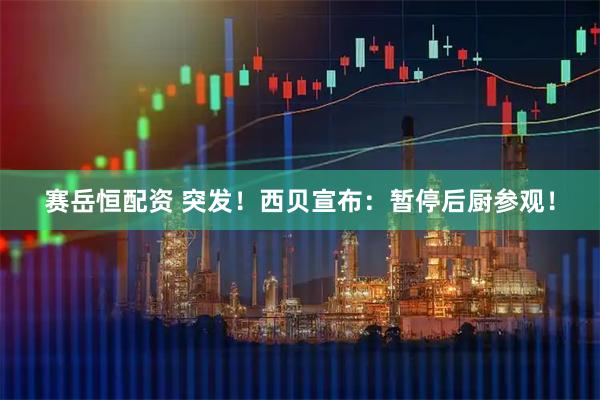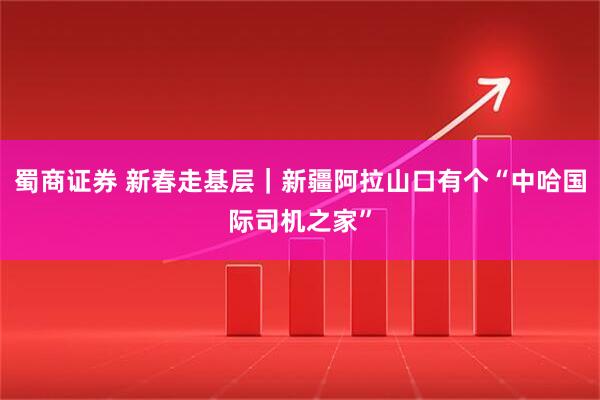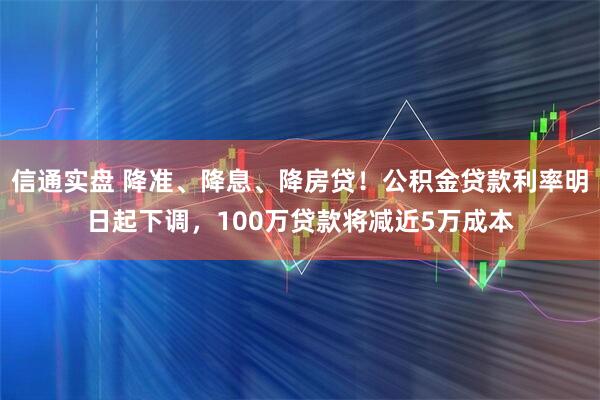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,正在研究室加班的我,突然被办公室的固定电话惊到了,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的美国号码。拿起电话,话筒里传来一口流利却带着几分生硬的中文:“您好汇盈配资,我是美国FDA专员,我们在抽检您出口的胰维康胶囊时,发现成分表中有‘紫河车’,请您解释一下,紫河车是什么东西?”
我握着听筒的手瞬间僵住了,冷汗顺着后背直往下淌。当时我有8款与大健康相关的产品出口美国,经销商又将其销往欧美十几个国家,凡华人集中之地,几乎都能见到这些产品的身影。它们一直以“膳食补充剂”身份合规通关,却没料到会在“紫河车”上栽了跟头。电话那头是位美籍华人,后来才知他祖辈早已移民,对中国传统药材并不十分了解。
自认为有点小聪明的我,此刻彻底慌了神。若如实告知“紫河车是人体胎盘”,以美国对人道主义和食品安全的严苛标准,这批货不仅会被扣押,后续出口资格可能被取消,甚至会被列入美国进出口黑名单。情急之下,我只能随口应付:“是羊胎盘。”本想蒙混过关,可对方紧接着追问:“羊胎盘属动物制品,是否通过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批准?”
我确实没办过这项检疫。此前出口时,美国海关多默认这类成分属“传统草本补充剂”,从未深究。别说那些“洋鬼子”,就是国人,又有多少能分清紫河车与草河车?
挂了电话,我立刻联系美国代理商和检疫部门,得到的答复是“补办手续至少需要半年左右”,而这批产品在海关的滞留期仅有45天,超期便会被销毁。那段时间,我每天盯着手机等消息,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,生怕几年的出口生意毁在这一次疏忽上。没想到第36天那个晚上,那位美籍华人再次来电,语气缓和了不少:“我们核查了您8年来的出口记录和多次抽检报告,无任何违规记载,按美国‘首违不罚’原则,允许您在FDA工作人员监督下更换标签,去掉‘紫河车’相关表述,但后续产品绝不能再添加与紫河车相关的原料。”
展开剩余78%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我连夜赶制新标签汇盈配资,通过国际航班直接送达美国,在当地代理协助下完成更换。
这批货最终顺利通关,可“紫河车”风波像根刺,始终扎在我的心里。
疫情过后的一天,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中年男人找到我在北京国贸的办公室,递来的名片印着“FDA食品药品审查专员”,括号里标注着中文名“李伟”。直到他开口,我才知道他就是当年打电话的那个人:“我这次来中国,一是拜访长期合规出口草本补充剂的企业,二是想和您聊聊上次的‘紫河车’,还有中西医的事。”落座后,李伟直言不讳:“我从小生在美国,很少回国。我一直不明白,药就是药,医就是医,可中国人为何非要把医分成中医和西医、中药和西药?还有更邪门的是:把中医中药又分为藏医藏药、苗医苗药、蒙医蒙药等等,你们这么分,是不是脑子有病?当年解放军进西藏,带去那么多军医,不就是因为西藏缺医少药?这么分,是弘扬先进,还是保护落后?在FDA所在地马里兰州,我接触过不少开诊所的中国民间医生,说起西医就气不打一处来:什么西医‘图财害命’,西医‘治不了大病’,什么‘将来还得靠中医拯救全人类’。”
我一时语塞——确实有不少人抱着“非此即彼”的态度看待中西医。李伟见我不语,又抛出让我更加无言以对的问题:“你说黄连素是中药还是西药?麻黄素是中药还是西药?胰岛素是中药还是西药?”
我下意识答:“复方黄连素是中药,盐酸黄连素是西药。”
可话音刚落,他就穷追不舍:“青蒿素从青蒿里提取汇盈配资,算中药还是西药?你们用双盲试验验证青蒿素疗效,这不又是西医的方法吗?”
那天的谈话,我全程处在被动和尴尬的境地。虽心有不甘,却找不出有力的反驳。直到李伟告辞时说:“我不是要否定中医,只是觉得你们把‘分类’看得太重,忘了医学的本质是救人。非要争个你高我低,这不过都是一群井底之蛙!”
后来我才知,李伟这次来中国还去了洛阳白马寺骨科医院,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:一位年长的中医正在给大腿摔伤的小伙子正骨,配文写道:“伤筋动骨一百天?抬着进来,走着出来,西医做不到的,中医真的可以做到。”
行文至此,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“安宫牛黄丸事件”——该双盲试验由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团队完成。该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,纳入300名中度至重度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,旨在探讨安宫牛黄丸对中重度脑梗死患者的疗效。研究结果发表在《中华医学杂志》英文版上,显示安宫牛黄丸在减少脑梗死体积、脑水肿以及90天后神经功能恢复方面,与安慰剂组相比并未显示出显著差异。
如此结果,让包括我在内的中医人自然是“一百个不答应”“一万个不答应”。可很少有人想过,双盲试验的核心是“标准化”,中医的核心是“辨证施治”。协和医院选取的试验人群,或许根本就不符合安宫牛黄丸“开窍醒神、凉血解毒”的适应症,效果不理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就像白马寺的中医治跌打损伤,不会给粉碎性骨折患者只靠推拿去解除伤痛,而是结合西医固定手法;西医处理慢性疼痛,也会建议患者试试针灸——这才是医学该有的样子:不执着于“标签”,只专注于“效果”。
我认识一位国医大师,前些时感冒咳嗽,他没硬扛着只喝中药,先去医院化验,查出是新型冠状病毒后,立刻口服阿奇霉素+咳特灵+复方甘草片,不到两周就痊愈了。他说:“有咳不仅仅是病毒感染,一定也有细菌感染,抗生素能快速杀菌,这是西医的优势;中药能调理体质、减少复发,这是中医的长处。非要问我中医好还是西医好,我只会说中西医结合最好!”反观现在,有些人为维护“中医纯粹性”,坚决不碰西药;有些人为证明“西医科学性”,全盘否定中医——这不是“守护医学”,而是“保护落后”。这正像李伟说的那样:“你分瑶医、藏医、苗医,分中医、西医,可在病人眼里,能缓解病痛、治好病的,就是好医。”
再回头看二十年前那批被FDA扣押的胰维康胶囊,后来我去掉紫河车,添加了西医证实可辅助降低糖尿病风险的维生素C、增强胰岛素敏感的维生素D、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维生素B12。产品不仅顺利出口,还成了美国市场的畅销品,原因是效果比添紫河车时更理想。用美国客户说:“我不管它是中药还是西药,吃了不用打胰岛素,这就是好药。”
“容乃公,公乃全”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,老祖宗的智慧早已道破真谛。医学从来不是“非此即彼”的战争,而是“各取所长”的“和光同尘”。西医的双盲试验能为中药有效性提供数据支撑,何乐而不为?中医的辨证施治能让西药治疗更具针对性,又有何不妥?西医手术能解决急性病症,中医调理能改善慢性问题——就像白马寺的推拿手法配西医石膏固定,就像国医大师既用中药又用抗生素,它们从不是对手,而是并肩救人的战友。而那些执着于“中西医之争”的人,说是夜郎自大也好,井底之蛙也罢,盲人摸象也好,盲人瞎马也罢,说到底,都是外强中干,内心不自信的彻底大暴露。他们把医学当成了争高低、论输赢的赛场,却忘了医学从诞生那天起,唯一的使命就是“救死扶伤”。当一个医生眼里只有“中医”或“西医”的标签,而非“患者”的需求;当一种医学追求的是“压倒对方”,而非“精进疗效”,那它早已偏离了医学的本质,成了束缚进步的枷锁。
要知道,患者躺在病床上,不会问救他的是中医还是西医,只会问“能不能治好我的病”;老百姓面对病痛,不会管药是中药还是西药,只会管吃了有没有用。我们争了这么多年的“中西医高下”,可在生死面前,这些争论何其可笑,何其苍白!在医学的殿堂里,不该有门户之见,不该有派系之争,只有“能治病”与“不能治病”的区别,只有“为患者”与“不为患者”的分野。
放下那些无谓的标签吧,让中医的智慧与西医的技术携手,让古老的传承与现代的科学融合——这不是对某一种医学的妥协,而是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,是对医学最本质的回归。唯有如此,医学才能真正成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屏障,而不是互相倾轧的工具;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在面对疾病时,拥有更多的办法、更大的底气,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医学的庇护下,活得更有尊严,更有质量。这,才是医学该有的模样,才是对老祖宗“和光同尘”智慧最好的践行!
苏清杰简介:
鲵龄源发明人。军旅16年,两次荣立二等功汇盈配资,八次三等功。离开部队后先是在两家知名医学院校任中医疑难病研究室副主任、主任、研究员,后在全国性公益基金管委会任常务副主任、主任,并两次列入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。现柏年中科首席科学家,国际旅居康养协会名誉会长、专家团首席专家。并有《国医大解读》等9部书稿出版,其中《临床血流变学》(合著)列为全国医学高等院校本科教材,《汉语编程基础》(合著)列入全国280多家大中院校计算机专业必修或选修教材。正在撰写近30万言的科普新作《新医林改错》。
发布于:北京市天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